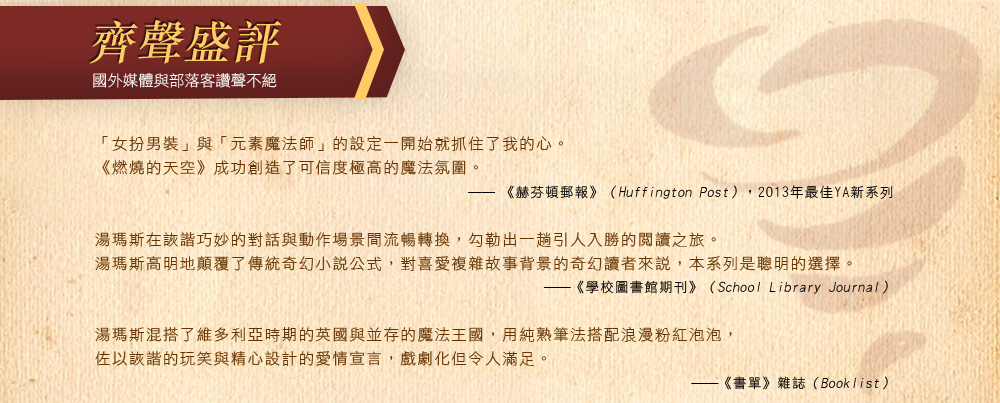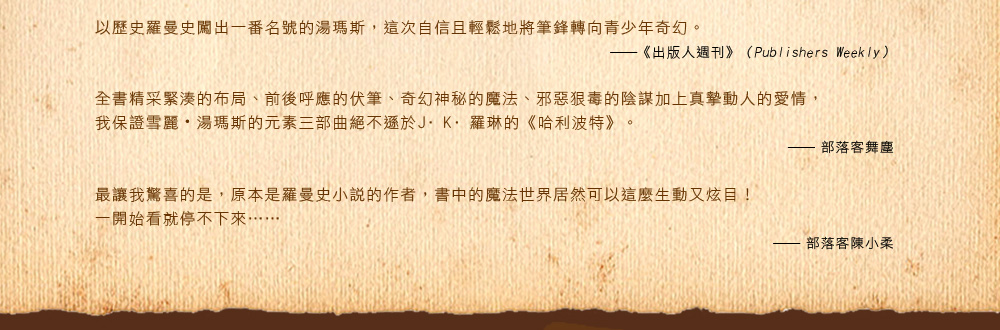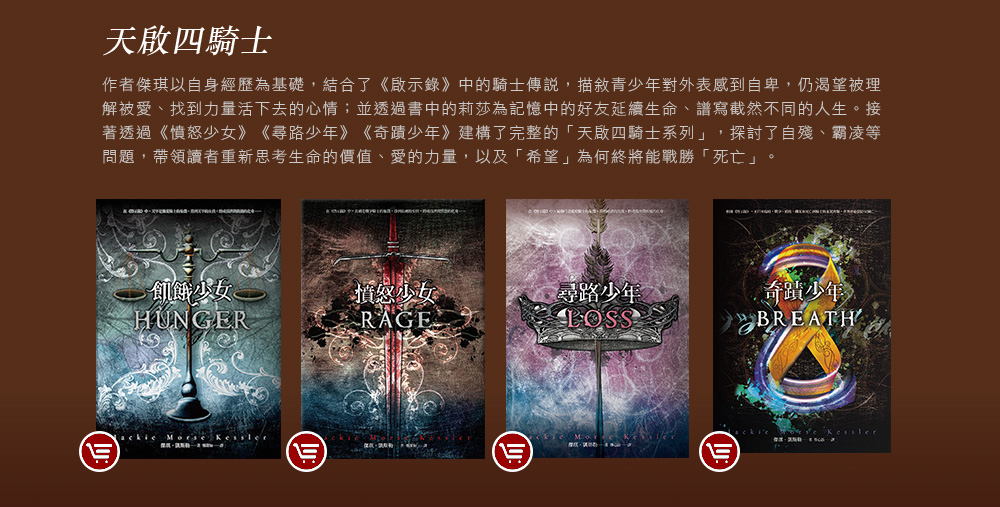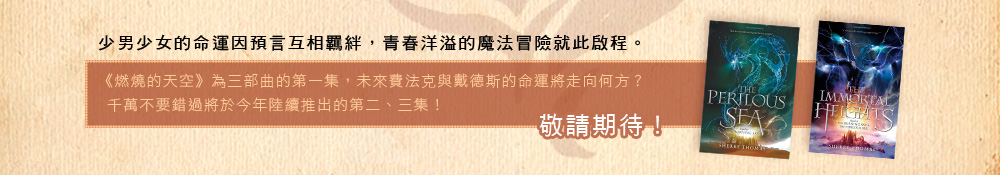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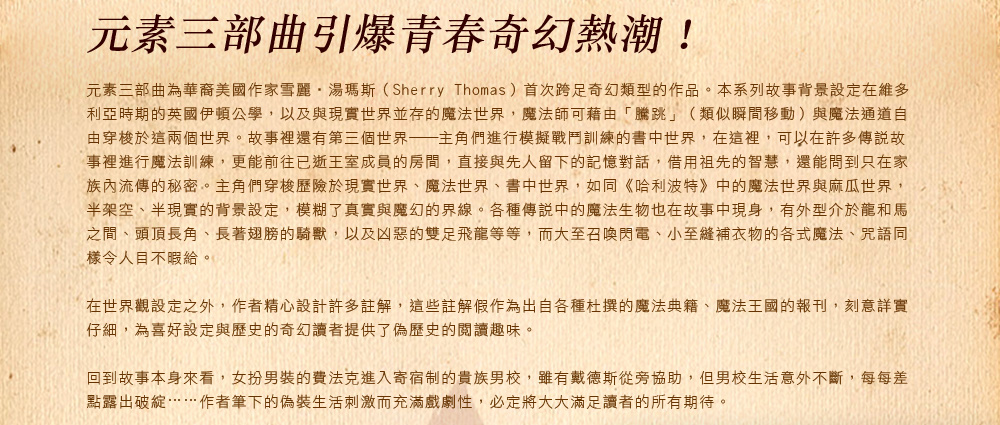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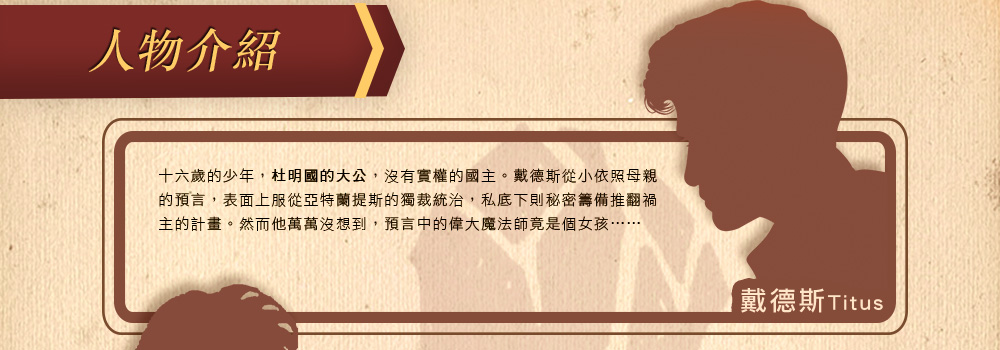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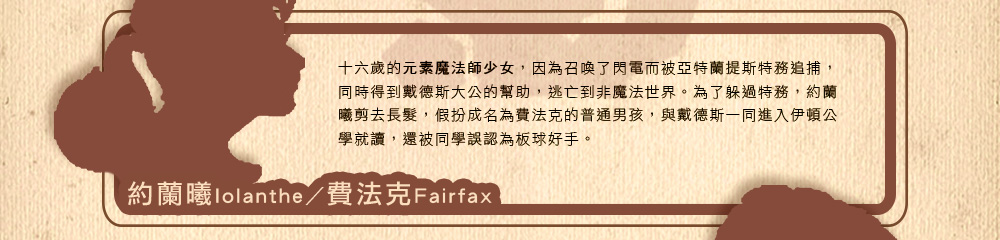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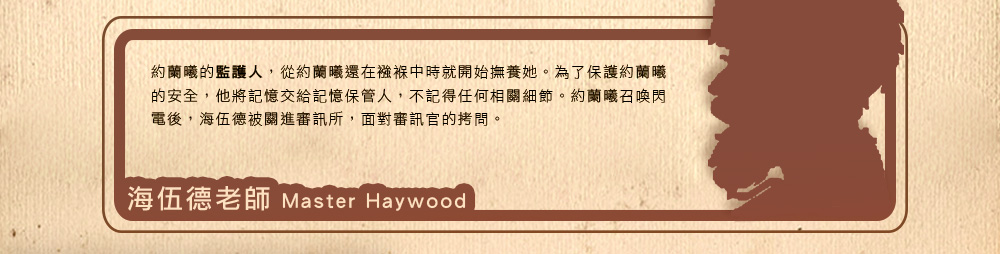
在真實世界裡,戴德斯的家建於迷宮山脈高聳的一道橫嶺之上,是所有魔法王國中最著名的城堡,遠比睡美人住過的城堡更加宏偉華麗。從陽台望出去,壯麗的風景盡收眼底:娟秀如緞帶的細長瀑布從幾千呎的高度垂掛下來,由高山白雪所灌注的小湖錯落有致地散布在藍色山腳下,而遠方的肥沃平原則是這個國家的穀倉。
然而,他對眼前的美景視而不見。這陽台使他緊張,因為預言說,他將在此處走入他的命運。那也將是結束的開始,因為他在預言裡的角色是導師和墊腳石──而且活不到這場遠征的終點。
幾名侍從在他身後聚集,他們的腳在地上摩擦,絲質外袍發出窸窣聲。
「殿下,您要喝點什麼嗎?」第一侍從吉勃斯以諂媚的語氣詢問道。
「不用。替我準備動身的東西。」
「我們還以為殿下明天早上才出發。」
「我改變想法了。」他的侍從有半數領亞特蘭提斯的薪水,他因此隨時找他們的麻煩,動不動就改變想法。有必要讓他們相信他是個自私又善變的人。「退下。」
眾侍從退到陽台邊緣,但仍繼續監視著他。除了臥室與浴室,他幾乎隨時隨地受到監視。
他的眼光往地平線梭巡,充滿恐懼地等待著那樁尚未發生,但已經左右了他一生的事件。
□
約蘭曦選了位於小石磨村東方幾哩的日落岩山頂。
她與海伍德老師搬來這個村子已快八個月,將近一整個學年,然而中南邊陲這塊由深谷、陡坡和急流組成的險峻地形,仍然美得令她屏息。他們的村莊已是文明最邊界的崗哨,再過去就是連綿的自然荒野了。
村民在日落岩的山頂,也就是附近地區的最高點,立了一支旗杆,讓杜明國的旗幟隨風飄揚。藍寶石色的旗幟在風中飄動,旗幟中央的銀色鳳凰在陽光下熠熠生輝。
約蘭曦跪下來時,膝蓋壓到某個又冷又硬的東西。她用手撥開旗杆基座下的草,看見一塊黃銅金屬匾鑲在地上,上面刻了幾個拉丁文:DUM SPIRO, SPERO.
「一息尚存,就有希望。」她喃喃地翻譯給自己聽。
而後她注意到銅匾上的日期:一○二一年四月三日,這一天見證了蘇琳女爵被處死、溫特維爾男爵遭放逐──代表「一月起義」功敗垂成的事件,那是杜明國民第一次,也是僅有的一次,以武裝行動反抗實質統治者亞特蘭提斯。
飛揚的旗幟並無特殊之處,至少沒被亞特蘭提斯判為違法。然而,這片埋在杜明國此一無名角落、紀念革命的銅匾,卻是反抗行為。
起義那年她六歲。海伍德老師帶著她加入離開首都迪拉瑪的逃難隊伍。他們在巨蛇山遠側難民營的臨時收容所住了幾個星期。大人都很焦躁,壓低聲音說話。小孩子則幾乎玩瘋了。
突然間,他們莫名奇妙地恢復了正常的生活。沒人提起魔法藝術研究學院裡該整修的損毀屋頂和翻倒的雕像,沒人提起發生過的任何事。
約蘭曦曾碰見一個在難民營認識的女孩,她們只笨拙地向對方揮揮手,便尷尬地轉身離去,彷彿那段時間做了什麼羞愧的事。
接下來幾年,亞特蘭提斯加強了對杜明國的控制,對外切斷他們與外面世界的聯繫,對內則利用在明的通敵者與在暗的祕密間諜建立起廣大的網絡,擴張其勢力範圍。
她不時會聽聞麻煩離家鄉越來越近:認識的人被懷疑行為有違亞特蘭提斯的利益,因此失去了生計,同學的親戚因被抓入審訊所而失蹤,鄰居突然遷往杜明國最偏遠的某座島嶼。
新的革命運動正在醞釀的謠言也時有所聞。幸好海伍德老師都沒有興趣。亞特蘭提斯彷彿是天氣,或這塊土地的地勢——人們並不試圖使其改變,只是去適應。
她降下旗幟並摺疊起來放在一旁,以防損壞。她一時有點擔心這樣把火和水一起展現,是不是真的會為自己帶來危險。不,應該不會。他們搬來小石磨村的頭兩年,隔壁鄰居就是一家影響力不大的通敵者,而海伍德老師從未禁止她在小朋友面前施展火把戲。
她把大釜靠在旗杆旁,讓大釜更容易接收閃電的震撼。然後,為了安全起見,她邁開五十大步。
總要以防萬一。
她訝異自己竟對可能發生的事情做好萬全準備。沒錯,若用一般標準來衡量,她的確是個還不錯的元素魔法師,但是和那些大師根本沒得比。她怎會以為自己可能完成只在傳說裡聽說過的成就?
她注視著萬里無雲的天空,深吸一口氣。說不出為什麼,但她打從心底知道《藥劑大全》裡的那位無名氏的建議並沒有錯。她只需要一道閃電,就能復原毀掉的彩光藥劑。
只是,閃電要怎麼召喚?
「閃電!」她伸出食指指向天空,大叫了一聲。
毫無動靜。她當然也不敢期待第一次嘗試就有結果,不過還是有點洩氣。或許把畫面想像出來會有幫助。她閉上眼睛,想像一道劈啪作響的雷電連接天空和地面。
仍然毫無動靜。
她把罩衫袖子往上推,抽出口袋裡的魔杖。她的心跳加快;在此之前,她施展元素魔法時從未使用魔杖。
魔杖是魔法力量的放大器;法力越強,放大的效果也越強。如果她再度失敗,那就是徹底的失敗了。不過,如果成功了……
她顫抖的手舉起魔杖,筆直地指向頭頂的天空,盡全力深吸一口氣。
「殛打大釜吧,拜託呀!我沒時間啦!」
第一道微光在極高空出現,而且似乎遠在另一片大陸之外。一道白色的火以之字形橫過弧形天穹,在無雲的深邃藍天形成優雅的弧線。
弧線對著她筆直落下──明亮又熾熱的死亡。
□
一道純白的光乍然出現,因為太過遙遠,看來只有一條線,卻如此熾亮,幾乎令戴德斯的眼睛瞎了片刻。
他驚駭地靜立了整整一分鐘,才覺得胸口像被什麼東西狠狠踢了一腳──這就是他等了大半輩子的那個徵兆啊。
他的手握成拳:預言成真了。但是他還沒準備好,他永遠都不可能準備好。
然而,不管是否準備好,他採取了行動,轉身往屋內走。
□
約蘭曦仰躺在地,眼睛好像瞎掉了,臉頰灼燒,她的耳朵裡似乎有響個不停的除夕夜鐘聲。
既然如此,她應該還活著。她呻吟著側轉身體,慢慢跪坐起來,但仍低頭用雙手摀住耳朵。
片刻之後,她張開眼睛,眼前是片綠色的布,那是她的裙子。她稍微抬起頭,雙眼逐漸對焦,她才看見自己的手。手擦傷了,但沒有流血。她如釋重負地嘆一口氣。原本她好擔心耳朵流血,更擔心自己會在手上發現一小部分腦髓。
不過,她周遭的草全是棕色的。這可奇怪了,懸崖上的荒原因為春天的到來早已是一片欣欣向榮的綠色。她的目光沿著乾枯的草地望過去──
旗杆不見了,黑煙從原本旗杆所在、同樣黑漆漆的地洞裡裊裊往上飄。
她奮力站起來,把魔杖塞回口袋,搖搖晃晃地往那冒著煙的地洞口走去,感覺自己的腿彷彿是玉米粥做成的。黑煙熏得她淚水直流,火絨般又脆又乾的草在靴底下嘎吱嘎吱作響。
那個洞大約十呎寬,深度和她的身高差不多;旗杆歪斜地橫躺在內。這真是太瘋狂了。閃電打下來的時候,電荷應該已經安全地導散到地底下了。
然後,她看到大釜,端端正正地坐在洞底,鍋中是她所見過最美麗的彩光藥劑,宛如蒸餾過的星光。
笑聲從喉嚨裡迸發出來,難得一次,幸運之神終於對她微笑了。婚禮的銀色彩光將很完美。她將送上一場完美的表演──啊,這是一定的,她一定要去表演。而歐克博夫太太也許會原諒海伍德老師開的玩笑──哈!什麼她女兒的婚禮將沒有銀色彩光。
頭上嗖的一聲讓她往上看。一頭外型介於龍和馬之間、雙翅大張的野獸從上空飛掠而過。野獸從北方來,以驚人的速度往海邊飛去。然而就在她呆看著的時候,野獸的翅膀垂直拍動,前進的動作瞬間慢下來。
而後轉過來面對她。
□
戴德斯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他騰跳之後的落點非常接近閃電打下來的位置,不過坐騎飛得太快,他沒能看清楚站在黑色懸崖頂上的那個魔法師。但是現在他讓坐騎調頭過來……
黑色長髮有一半因為雷擊而豎立起來,縐巴巴的白色罩衫,綠色的裙子。千真萬確,召喚閃電從天而降的是個女孩。
女孩。
預言中的魔法師不能是女孩。天啊,他該拿女孩怎麼辦?